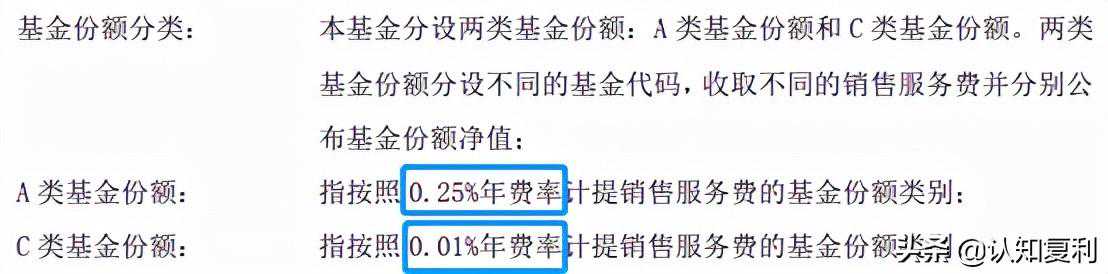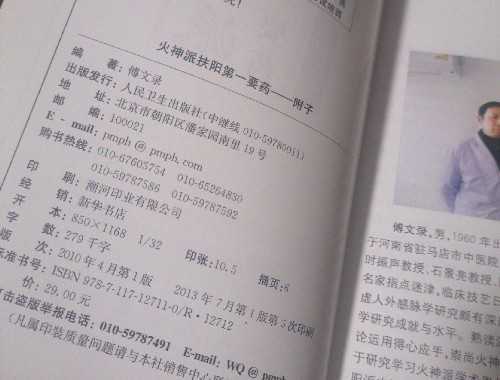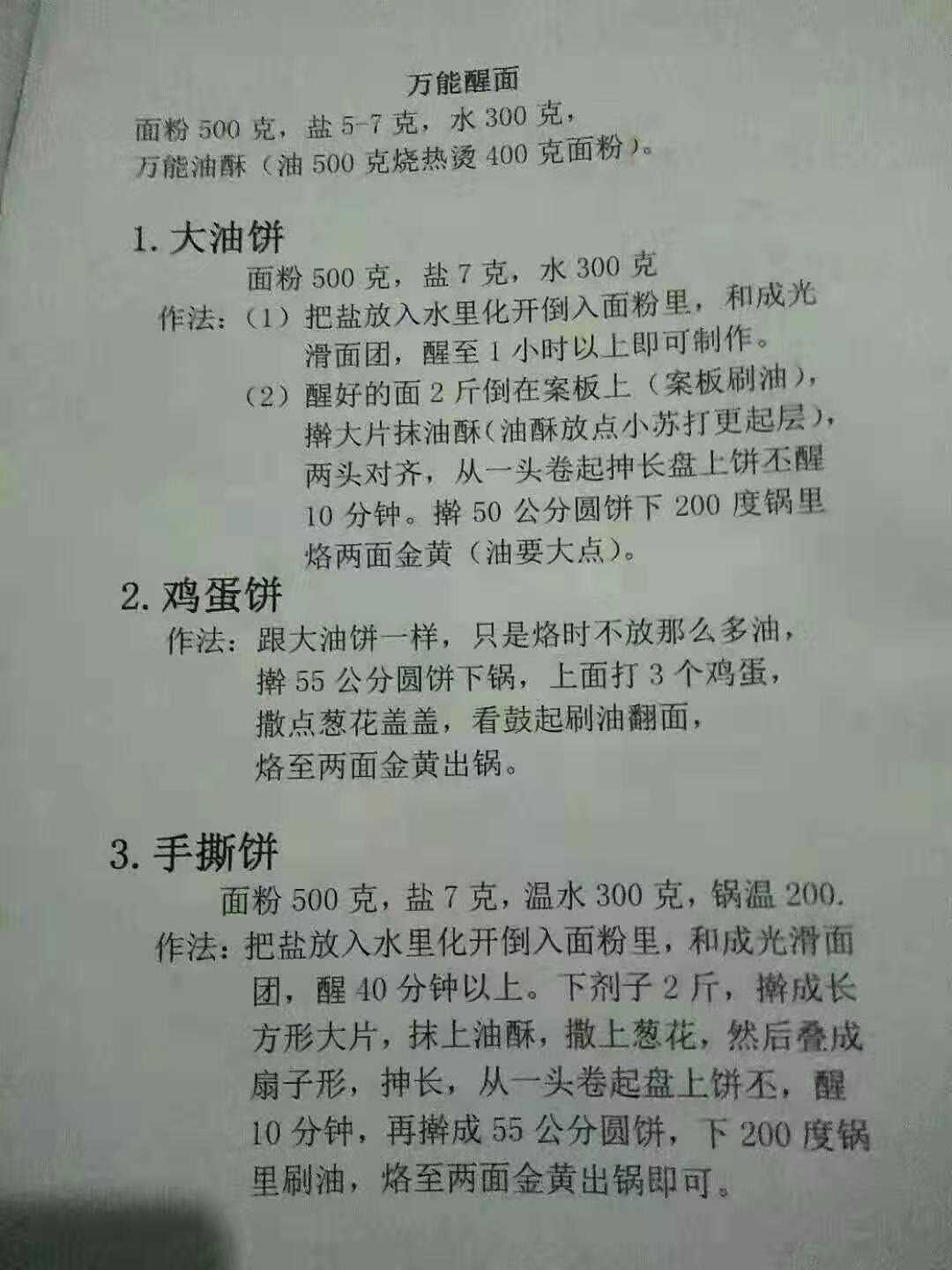伯母拦住了我,眼中闪着不出声的泪花。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了四十年来的隔阂源于何处。
我叫赵月芬,1978年生人,踏上回乡的公共汽车时,心里像揣了只兔子。自从那年春节在堂弟脸上留下疤痕,我就鲜少回老家了。
车窗外,麦田与杨树林交替掠过,北风卷着黄土扑打车窗,发出细碎的沙沙声。这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声音,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。
从县城到我们小岗村,以前要坐半天拖拉机,如今公共汽车只用了四十分钟。靠近村口时,我摁下车铃,司机师傅一脚刹车停在路边,招呼着:"大姐,到家啦!"
扑面而来的是熟悉的土腥气和冬日的寒意。我裹紧羽绒服,提着行李走在村口的水泥路上。四十年过去,当年泥泞不堪的土路变成了平整的水泥路,低矮的平房变成了二层小楼,井台和水桶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家家户户通上的自来水。
我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稍作休息。这棵老槐树已有百年历史,树干粗壮,树皮上布满沧桑的裂纹,就像是刻满故事的年轮。小时候,我们村里的孩子都喜欢在这棵树下玩耍,捉迷藏、跳皮筋、丢沙包。
"姐,你是赵根生家的大闺女吧?"一个骑着摩托车的中年人停在我面前,摘下头盔,露出一张黝黑的脸。
我仔细一看,才认出是邻居家的刘大壮,当年和我同班的男孩。"是我,月芬。大壮,你还认得我呢?"
"咋不认得!从小就是俺村的文化人。"刘大壮呵呵一笑,露出一口黄牙,"回家探亲呐?坐我的车,捎你一程。"
坐在摩托车后座,穿过熟悉又陌生的村道,我的心跳越来越快。路两旁的房屋几乎全变了模样,只有那些老槐树和村头的小河依旧如故。
"你赵家现在可好了,你堂弟小军是咱县一中的老师,有出息!你伯母没少在村里人面前夸他。"刘大壮边开车边回头说话,语气里满是羡慕。
"是啊,听说了。"我轻声应着,心里却泛起涟漪。小军,我那个曾经被我划伤脸的堂弟,如今成了受人尊敬的教师。
摩托车在一栋红砖青瓦的老房子前停下。这是我的娘家,在一片新建的小楼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房子虽旧,但院子打扫得很干净,门前种着几棵冬青,墙角还有几盆腊梅,傲然怒放。
我站在院门口,犹豫着要不要敲门。恍惚间,仿佛又回到了1988年那个雪花纷飞的春节前夕。那时候,改革开放十周年,人们的生活刚刚有了起色。大队广播站整天播放着"春风吹战鼓擂,万马奔腾"的歌曲,村里人脸上都带着憧憬。
那年春节,父亲从县供销社带回了一套《小人书》,是我们那个年代孩子们最珍贵的宝贝。那套书里有《岳飞传》《杨家将》《三国演义》,每一本都是我的心头好。
那天下午,我正在院子里的石桌上翻看《岳飞传》,六岁的堂弟小军来了,非要跟我一起看。我不肯给他,他就扯我的书。在争抢中,我手里的铅笔盒划过他的脸。鲜血顺着他稚嫩的脸颊流下来,染红了他的小棉袄。他的哭声,伯母的尖叫,父亲的呵斥,一切都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记忆里。
"月芬,是你吗?"伯母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。她站在院门口,头发已经全白,脸上的皱纹像是一道道沟壑。她比我记忆中要瘦小得多,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棉袄,脚上是一双黑色布鞋。
"伯母"我张了张嘴,喉咙发紧,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
"快进来,外面冷。"伯母拉着我的手进了屋。屋里温暖如春,一个小火炉在角落里轻轻燃烧,土炕上铺着厚厚的褥子,墙上贴着已经泛黄的春联。炕桌上摆着一把大红枣和几个苹果,还有一个旧铁盒。
"坐下歇会儿,我给你倒杯水。"伯母转身去了厨房,很快端来一杯热茶。茶水的热气在寒冷的冬日里显得格外温暖。
"伯母,我"我想道歉,却不知从何说起。四十年的愧疚积压在心头,一时难以言表。
"知道你要来,我特意把家里收拾了一遍。"伯母坐在炕沿上,脸上的皱纹在昏黄的灯光下更加明显,"你父亲去世那年,我就想去看你,可小军说你忙,怕打扰你。"
父亲五年前因病去世,那时我刚刚在城里安顿下来,工作忙碌,对家乡的联系少之又少。听到伯母提起父亲,我的眼眶湿润了。"对不起,伯母,我应该多回来看看的。"
"傻孩子,你有自己的生活。"伯母笑了笑,从炕桌上拿起那个旧铁盒,"这些年,你寄来的贺卡我都收着呢。"
她打开铁盒,里面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一沓贺卡,有国庆的、春节的、中秋的。每一张都是我从城里精心挑选,寄给家乡亲人的。看到它们被伯母这样珍藏,我心里既温暖又惭愧。
"我一直以为你们恨我。"我低声说,"特别是小军。"

伯母摇摇头,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张照片,"小军现在是县一中的老师,教语文。这是他去年获奖时的照片。"
照片中的男人西装革履,站在讲台前,脸上有一道明显的疤痕,从左眼角一直延伸到嘴角。那道疤,是我留下的。疤痕虽然随着岁月有所淡化,但依然清晰可见。但让我惊讶的是,照片中的小军目光坚定,嘴角带着自信的微笑,丝毫没有因为脸上的疤痕而显得自卑。
"他恨我吗?"我忍不住问道。
"恨过。"伯母坦率地说,"上中学时,他因为这道疤自卑,不愿意见人。有同学取笑他,叫他'刀疤脸'。那时候,他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,不肯上学。"
我低下头,心如刀绞。我从未想过自己一时的任性会给堂弟带来如此长久的痛苦。
"有一次,他放学回来,衣服都撕破了,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。原来是和嘲笑他的同学打了一架。"伯母叹了口气,"那天晚上,你爸来了,和小军聊了很久。从那以后,小军好像变了一个人。"
我抬起头,疑惑地看着伯母。
"你爸跟他说,疤痕是命运的印记,不必掩饰,反而该让它成为动力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疤痕,有的在脸上,有的在心里。真正的勇气不是没有疤痕,而是带着疤痕依然昂首挺胸地生活。"伯母的眼睛湿润了,"从那以后,小军开始努力学习,好像要证明什么。每次有人问起他脸上的疤,他都会说这是他的勋章。"
我默默流泪。父亲从未向我提起过这些事,但他却在暗中帮助着小军走出阴影。
"你爸还资助小军上了大学。"伯母接着说,"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,供不起孩子上大学。你爸每个月都寄钱来,说是单位发的补贴,让小军安心读书。直到后来小军工作了,我们才知道那些钱其实是你爸自己省下来的。"
听到这里,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泪水夺眶而出。父亲在我面前从未提起过这些事,但他却默默地承担着责任,弥补着我造成的伤害。
晚饭时分,堂弟小军回来了。他比照片上要沧桑些,眼角有了细纹,但那双眼睛和小时候一样明亮。"表姐。"他喊我,声音低沉而温和。
我不敢与他对视,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。"小军,我"我想道歉,却不知从何说起。
他摆摆手,从背包里拿出两瓶啤酒,坐到我对面。"知道吗?当年我恨你。"他直言不讳,"上初中时,女同学们看到我的疤就躲开,男同学们叫我'刀疤脸'。那时候,我天天对着镜子,想着如果没有这道疤,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。"
我僵在原地,不知如何回应。
"但后来我明白,这道疤让我知道生活不会一帆风顺。"他倒了两杯酒,递给我一杯,"我十八岁那年,考上了师范学院,家里却拿不出学费。我打算辍学打工。是二叔——你父亲给了学费。他说,学业比什么都重要。"
我愣住了。父亲从未提起过这事。
"他还说,这是一家人的事,不必告诉任何人。"堂弟笑了,"包括你。"
小军喝了口酒,继续说:"二叔对我说,人这一辈子,受的伤不重要,重要的是伤好了以后,你变成了什么样的人。我记住了这句话,它改变了我的一生。"
我握紧酒杯,想起父亲严厉却又慈爱的面容。他曾经打过我,因为我伤害了堂弟;但他也默默地承担起责任,帮助堂弟走出阴影。这就是我的父亲,严厉中蕴含着无尽的温情。
"二叔去世那年,我正在省城参加培训,等我赶回来,已经来不及见他最后一面。"小军的声音哽咽了,"我一直后悔,没能好好谢谢他。"
我握住小军的手,泪流满面。"爸爸知道的,他一直为你骄傲。"
那天晚上,我们喝了很多酒,聊了很多往事。小军告诉我,他现在是县一中的语文老师,教高三毕业班。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,妻子是同校的数学老师,儿子今年上初中。他在县城买了房子,但老家的房子一直保留着,每逢周末和假期,他都会回来陪伴伯母。
"记得那套连环画吗?"小军突然问我。
我点点头。那套书是引发一切的源头,我怎么可能忘记。
"我还留着呢。"小军起身,从书柜里拿出一个布包,小心翼翼地打开,里面是那套已经泛黄的连环画。"二叔临走前给我的,说这是你最珍贵的东西,让我替他好好保管。"
我接过书,翻开发黄的书页,上面有我和父亲的笔记,还有一些童年时代的涂鸦。这套书承载了太多记忆,既有快乐,也有痛苦。
"表姐,明天我带你去看看村子吧。"小军提议,"这些年变化很大,你可能认不出来了。"
次日,小军陪我走遍了整个村子。村子比我记忆中大了很多,新建了学校、卫生室和文化广场。老人们在广场上打太极,孩子们在操场上奔跑嬉戏。经过村委会时,一群老人正坐在门口的长椅上闲聊,看到小军,都亲切地打招呼:"小军老师来啦!"
"这是我表姐,从城里回来的。"小军向他们介绍我。
"哎呀,是赵根生家的大闺女吧?都多少年没见了!"一位白发老人认出了我,"长得和你妈一模一样,标志!"
我有些腼腆地笑了笑,心里却感到温暖。在这个小村庄里,我依然是被记得的,是属于这里的一份子。
走到村头的小河边,我停下脚步。这条小河见证了我的童年,夏天在这里洗澡捉鱼,冬天在结冰的河面上滑冰。如今河水依然清澈,河边的柳树更加葱郁。
"小时候,我经常一个人来这里。"小军站在我身旁,望着远处,"每次被人嘲笑,我就跑到河边哭。有一次,二叔找到我,陪我一起坐了很久。他告诉我,男子汉流血不流泪。但其实,我看到他的眼睛也是红的。"
我沉默不语,心中五味杂陈。
回到家,小军提议修缮祖屋。"房子有些年头了,墙皮脱落,门窗也不严实,冬天冷得很。趁你在,我们一起修一修吧。"
于是,接下来的几天,我们一起刮墙、粉刷、修补裂缝。劳作中,话渐渐多了起来。他说起教书育人的喜悦,我讲述城市生活的快节奏。我们像两个普通的亲人,分享着各自的生活,弥补着失去的时光。
"知道吗?我做梦都想把这道疤抹平。"一天,小军指着自己的脸,"读大学时,我去医院咨询过整容手术,但最后还是放弃了。"
"为什么?"我好奇地问。
"有个学生问我,'小军老师,你脸上的疤是怎么来的?'我说这是我表姐给的,他问'你恨她吗?'我突然不知如何回答。"小军停下手中的活,望向窗外,"那一刻我才明白,恨一个人比原谅一个人要耗费更多精力。何况,是亲人呢?"
他转过头,真诚地看着我:"后来我想明白了,这道疤让我变成了今天的自己。如果没有它,我可能不会那么努力,不会成为一名老师,不会有今天的生活。所以,我要谢谢你,表姐。"
我无言以对,泪水再次涌出。四十年的心结,就这样被轻轻解开了。
修缮老屋的那几天,我们谈了很多,笑了很多,也哭了很多。我们一起翻看老照片,一起回忆童年,一起为父亲母亲扫墓。小军带我去了父亲的坟前,我们献上鲜花和酒,向这位深沉而伟大的父亲表达敬意和思念。
伯母看到我们和好,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了许多。她拿出珍藏多年的老物件,给我们讲述那些我们不知道的往事。原来,在我们不知道的岁月里,父亲和伯母一直保持着联系,他们共同守护着这个家,守护着我和小军的成长。
"你爸临走前,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"伯母告诉我,"他怕你一个人在城里太孤单,经常让小军打电话去问候你。只是你太忙,很少接电话。"
我这才明白,为什么会有那些莫名其妙的来电,为什么会有寄到单位的节日贺卡。原来,我从未被遗忘,从未被放弃。即使我选择了逃避,家人依然在默默地关心着我。
正月十五那天,全家团聚。小军的妻子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,我们在温暖的灯光下共进晚餐。饭桌上,气氛热烈而温馨,话题从家常琐事到国家大事,从过去的回忆到未来的规划。小军的儿子小明问我:"姑姑,你能讲讲城里的故事吗?"
我笑着点头,给他讲述城市的高楼大厦,繁华的商场,拥挤的地铁。小明听得入迷,眼睛里闪烁着向往的光芒。
觥筹交错间,村里一个热情的长辈非要我喝酒。"赵根生的闺女,这么多年没回来,今天必须喝个痛快!"他举着杯子,眼睛笑成一条缝。
就在我为难时,小军站了出来。"李叔,我表姐不胜酒力,我来替她喝。"他举起杯,冲我一笑,"表姐给我的不只是疤。"
那一刻,我明白了小军的用意。这不仅仅是一杯酒,更是一种和解,一种原谅,一种新的开始。
饭后,我们站在院子里放烟花。烟花绽放的瞬间,照亮了夜空,也照亮了我们的脸。我看到小军脸上的疤在夜色中若隐若现,就像是命运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印记,深刻而又意味深长。
"表姐,以后多回来看看。"小军站在我身旁,声音温柔,"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"
我点点头,看着夜空中绽放的烟花,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希望。四十年前,我在堂弟脸上划下的那道疤,曾经是我心中的痛;四十年后,它成了我们之间特殊的纽带,见证了我们的成长和和解。
那晚,我住在老家的土炕上,听着窗外的风声,想起父亲的教诲,想起小军的宽容,想起伯母的坚韧。我明白,生活就像这四季轮回,有春暖花开,也有秋风萧瑟;有阳光明媚,也有风雨如晦。重要的是,无论遇到什么,我们都能带着自己的"疤痕",勇敢地面对生活,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。
离开前的那天早晨,我站在院子里,看着东方的朝阳缓缓升起。小军走到我身旁,递给我一个手工制作的木盒。"打开看看。"他微笑着说。
我打开木盒,里面是那套已经修复过的连环画,旁边还有一封信。信是父亲生前写的,信中说:"月芬,无论你走到哪里,记得回家的路。家永远在这里等你。"
我紧紧抱住小军,泪水再次模糊了视线。我知道,这次回家之旅,不仅治愈了四十年的伤痛,也让我找回了自己的根,找回了家的温暖和亲情的力量。
"表姐,我们永远是一家人。"小军轻轻拍着我的背,声音坚定而温暖。
是啊,我们永远是一家人。即使有过伤害,有过误解,有过隔阂,但血浓于水的亲情依然将我们紧密相连。这份连接,穿越时光,跨越距离,历久弥新。
回城的车上,我望着窗外渐行渐远的故乡,心中不再有愧疚和遗憾,只有满满的温暖和感恩。我知道,无论未来如何,我都会经常回来看看,因为这里有我最珍贵的亲人,有我最深切的牵挂,有我永远的家。